当高光褪去之后:CXO还能狂奔多久?

秘丛丛 郑洁丨撰文
旧梦丨编辑
作为药明康德当年回国时唯一的竞争对手,CRO龙头康龙化成,曾一度被认为是MNC巨头牵制药明系无序发展的利器——对于这种像药明一样外企需求导向型CRO公司,需要扶植一个“备胎”来防止龙头的垄断。
然而,这家长期在药明系光环掩盖下的CRO龙头,在7月18日中报业绩预告发布后的第二天,股价盘后6分钟内跌了接近19%,这一刻,仿佛能看到千军万马在往外撤,还有投资者满头问号,“撤也不是抄底也不是,煎熬了一整天。”
当天,康龙化成领跌CRO板块,连续两天也没有缓过劲儿,很多人感叹中国的医药CRO行业遇到了挫折,“医药外包研发业务是不是不大好了?”
CRO作为过去两年整个医药二级市场涨得最好的板块之一,良好的景气度让它成了投资人和创业者前赴后继的一个细分赛道。但成也景气度,败也景气度。如今CRO板块高企的估值,使得这个板块动不动就上演若干资本鬼故事。
而这一次康龙化成低迷的业绩增长,似乎也预示着整个中国的CRO板块在起楼宴客之后,会不会像既有的故事那样,因为渗透率见顶和产能过分扩张带来一地鸡毛?
-01-
另一个龙头:康龙化成的20年
如果要将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波动上升到整个中国的医药CRO行业遇挫的高度,研究这个命题的真伪,需要拉长视野来看,但拉长视野并不太容易,因为“中国的医药CRO行业”发展至今,也不过20年的时间。
21世纪初,当李革从美国药典转身回到江苏无锡创立药明康德时,浙江人楼柏良也看到了历史的机遇。2002年,由于一次到北京作学术报告的机会,楼柏良被国内的“活力”震撼,动了回国创业的念头。
楼柏良是化学专业出身,曾经当过两年化学老师。1983年,楼柏良进入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,取得硕、博学位,之后,他留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,取得学位后,楼柏良一直在美国的制药企业从事化学合成研究。
2000年前后,“国内新药研发领域基本空白,市场大有可为”,楼柏良看到了这一点,考虑到北京的科研实力以及弟弟对在北京做企业有经验的实际层面,楼柏良带着康龙化成的雏形来到北京中关村。
2003年,《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》发布,文件从法理上承认了CRO企业在中国的地位和空间。当时的高层仿佛洞悉了美国回国创业的科学家们的需求,政策如同及时雨,对CRO行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政策“开道”,康龙化成也迎来迅速发展。
创始人的专业出身决定了企业的起步基因,当时“新药发现”技术在国内刚起步,康龙化成刚好弥补了这一点,从实验室化学起步,研发领域主要集中在药物小分子有机合成、药物化学、研发生物学、制药工艺研究、病理毒理等方面。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行业前几名的龙头,默克、辉瑞等跨国制药企业也成为其客户。
之后的10年,是CRO企业逐步完善框架、扩张版图、联通上下游的10年。一边引入外部资金诸如行业“一哥”药明康德的CRO服务从药物发现向临床前药物测试、临床试验以及商业生产延伸,康龙化成一边引入外部君联资本,一边在业务上也由实验室化学拓展生物科学、CMC/CMO 业务延伸,逐步完成CRO一体化业务构建。
蛰伏一段时间后,属于这个行业的风又起了。2015年,“722数据核查”开启,标准化CRO公司又看到了新的机会。
紧接着,国家鼓励医药创新研究的帷幕拉起,2017年,《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》出台,中国也在这一年加入ICH(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会),新药审批速度不断加快,仿制药端的空间则被集采逐渐压制。
同年,热钱资金涌入,CRO企业开始扎堆上市,康龙化成也在这时候递交了IPO文件。2018年,康龙化成IPO获通过,随后,康龙化成A+H两地上市。之后,康龙化成开始构造更全面的全球化战略,收购交易接二连三:2020年,康龙化成收购了美国一家CRO公司Absorption Systems,2021年,康龙化成宣布收购了艾伯维在英国的生物药生产工厂Allergan Biologics Limited。
今年1月,康龙化成收购英国的原料药生产基地Aesica Pharmaceuticals Limited,5月,康龙化成又宣布收购安凯益博和美国Noramco的原料药生产基地。
CRO的狂奔也表现在了资本市场。
过去几年,CRO的风口地位已经人尽皆知,二级市场上,一位投资者在买入康龙化成时,看中的是其仅次于药明康德的CRO“龙二”地位、国内创新药研发的灿烂前景、海外CRO业务向海内转移的潜力,但就在当年年底,新冠疫情在全球开始大流行,情况由此开始转变。
回过头看,新冠疫情、Biotech投资热浪退潮、国内创新药企资金告急、医药CRO龙头业绩大挫……这几个现象互为因果,有明确的逻辑关系。
作为创新药行业的服务方,迭代更新的速度需要比创新药更快才能脱颖而出。但是所有人都低估了创新药在国内变化的速度:PD-1从上市到降到白菜价前后不过四年。这些需要“建产能——招人——投产”的CRO公司,步子卖得更快,也更难收回。
-02-
快速发展后的急转弯:CRO的瓶颈期
如果要将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波动上升到整个中国的医药CRO行业遇挫的高度,研究这个命题的真伪,需要拉长视野来看,但拉长视野并不太容易,因为“中国的医药CRO行业”发展至今,也不过20年的时间。
21世纪初,当李革从美国药典转身回到江苏无锡创立药明康德时,浙江人楼柏良也看到了历史的机遇。2002年,由于一次到北京作学术报告的机会,楼柏良被国内的“活力”震撼,动了回国创业的念头。
楼柏良是化学专业出身,曾经当过两年化学老师。1983年,楼柏良进入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,取得硕、博学位,之后,他留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,取得学位后,楼柏良一直在美国的制药企业从事化学合成研究。
2000年前后,“国内新药研发领域基本空白,市场大有可为”,楼柏良看到了这一点,考虑到北京的科研实力以及弟弟对在北京做企业有经验的实际层面,楼柏良带着康龙化成的雏形来到北京中关村。
2003年,《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》发布,文件从法理上承认了CRO企业在中国的地位和空间。当时的高层仿佛洞悉了美国回国创业的科学家们的需求,政策如同及时雨,对CRO行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政策“开道”,康龙化成也迎来迅速发展。
创始人的专业出身决定了企业的起步基因,当时“新药发现”技术在国内刚起步,康龙化成刚好弥补了这一点,从实验室化学起步,研发领域主要集中在药物小分子有机合成、药物化学、研发生物学、制药工艺研究、病理毒理等方面。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行业前几名的龙头,默克、辉瑞等跨国制药企业也成为其客户。
之后的10年,是CRO企业逐步完善框架、扩张版图、联通上下游的10年。一边引入外部资金诸如行业“一哥”药明康德的CRO服务从药物发现向临床前药物测试、临床试验以及商业生产延伸,康龙化成一边引入外部君联资本,一边在业务上也由实验室化学拓展生物科学、CMC/CMO 业务延伸,逐步完成CRO一体化业务构建。
蛰伏一段时间后,属于这个行业的风又起了。2015年,“722数据核查”开启,标准化CRO公司又看到了新的机会。
紧接着,国家鼓励医药创新研究的帷幕拉起,2017年,《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》出台,中国也在这一年加入ICH(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会),新药审批速度不断加快,仿制药端的空间则被集采逐渐压制。
同年,热钱资金涌入,CRO企业开始扎堆上市,康龙化成也在这时候递交了IPO文件。2018年,康龙化成IPO获通过,随后,康龙化成A+H两地上市。之后,康龙化成开始构造更全面的全球化战略,收购交易接二连三:2020年,康龙化成收购了美国一家CRO公司Absorption Systems,2021年,康龙化成宣布收购了艾伯维在英国的生物药生产工厂Allergan Biologics Limited。
今年1月,康龙化成收购英国的原料药生产基地Aesica Pharmaceuticals Limited,5月,康龙化成又宣布收购安凯益博和美国Noramco的原料药生产基地。
CRO的狂奔也表现在了资本市场。
过去几年,CRO的风口地位已经人尽皆知,二级市场上,一位投资者在买入康龙化成时,看中的是其仅次于药明康德的CRO“龙二”地位、国内创新药研发的灿烂前景、海外CRO业务向海内转移的潜力,但就在当年年底,新冠疫情在全球开始大流行,情况由此开始转变。
回过头看,新冠疫情、Biotech投资热浪退潮、国内创新药企资金告急、医药CRO龙头业绩大挫……这几个现象互为因果,有明确的逻辑关系。
作为创新药行业的服务方,迭代更新的速度需要比创新药更快才能脱颖而出。但是所有人都低估了创新药在国内变化的速度:PD-1从上市到降到白菜价前后不过四年。这些需要“建产能——招人——投产”的CRO公司,步子卖得更快,也更难收回。
-02-
快速发展后的急转弯:CRO的瓶颈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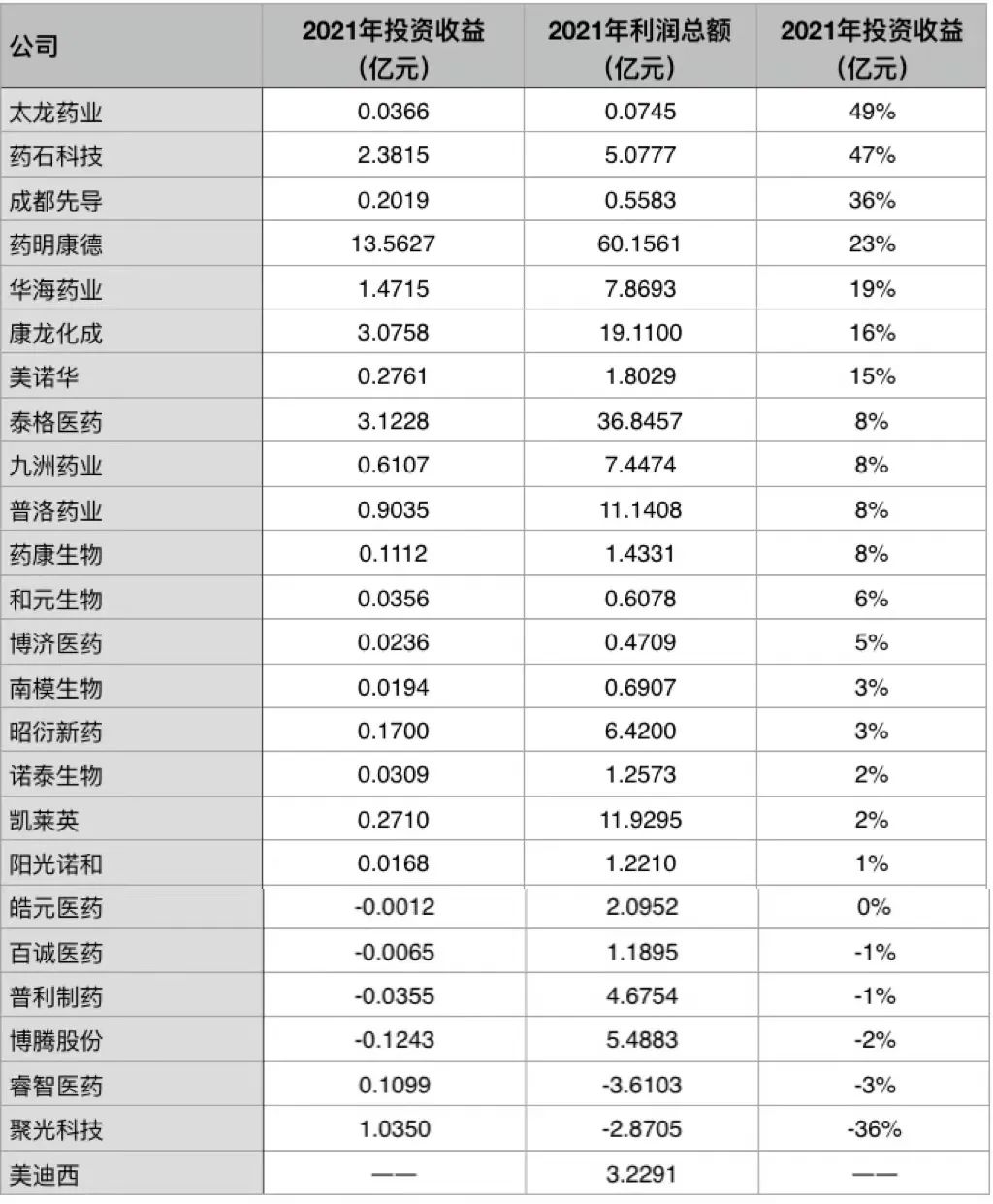
图片:代表CXO公司2021年投资收益情况
来源:整理自网络
CRO公司做投资,往好了说是公司利用股权绑定biotech的研发外包订单,但当这一块利润占比过大时,CRO如何去平衡投资和主业之间的关系,这对公司管理提出了一个挑战。
另一边,在“中国A股十年3000”点的情况下,投资收益注定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,反映在上市公司估值上就是一个忽高忽低的境况。
今年,康龙化成还没看到收购带来的真金白银,先体验了自己投资的公司估值下跌。根据康龙化成初步预算,2022年上半年其上市及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亏损了8000万。
而中国投资者的耐心,往往是按天计算。整个市场似乎容忍不了这种估值的大起大落。
-03-
创新药停滞: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
现在一个新的现实摆在面前,那就是创新药市场出现收缩。
首先是投融资的情况,2022年前5个月一级市场投融资事件数量和金额均呈下降趋势。投融资事件总计492起,同比减少45.8%;投融资金额达548亿元,环比减少50.9%。二级市场的再融资事件数和金额,更是从去年第三季度之后持续低迷。
而在药物获批方面,2022年上半年生物药获批数量同比增长16%,增速放缓,化药新药同比增长直接为负(-4%)。
这些需要长期烧钱的创新药企如今既借不到钱,商业化又遥遥无期,那自然也没有CRO的蛋糕可以吃。
“现在很多biotech都在砍自己的项目,如果管线的临床进度在国内排不到前几名,自己就直接停了。”据一位业内人士观察,最典型的例子来自港股上市公司——百奥泰、三叶草,它们已经聚焦自己排名靠前的管线,其他项目几乎都不做了。
她对于康龙化成净利润表现,没有感到太大意外。“如果CXO企业的订单多来自国内的biotech,随着这一波市场萎靡,业绩肯定会显著下滑。”
实际上,所谓的市场萎靡其实是对创新药估值逻辑的修正。另一位投资人看到,过去很多biotech公司忙于充管线,市场根据企业有多少个产品来估值。“它们从药明康德等公司的DDSU部门批发出来一系列的药,之后改改结构推到临床去融资。”以前市场认可这样的模式,可以给出较高的估值,如今已经不买单了。
一直以来,CXO全球产业链转移的逻辑之一就是“降低成本”。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相比,国内的CXO企业有长期竞争优势,其中最重要一点在于中国的工程师红利。
目前,欧美占全球CRO市场份额的90%左右,因此国内的CRO市场仅占不到1/10的份额。很多CRO企业都想分到海外市场这个大蛋糕,但现实是只有国内少数头部企业拿到了入场券,能接到一些国际大药厂的订单。
看上去,国内CXO行业的疯狂增长走到了转折点,以往的高光不可持续,它们还在寻找也亟需找到下个增长动力。
*声明:本文内容转载于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转载目的在于传递信息,并不代表本平台观点。如涉及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它问题,请与本网站留言联系,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!
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J7TkbkSwrTdf-aOFq9NmpA)



